2010年代幻想文学的主要趋势(上)1
三丰(译)
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,幻想文学似乎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新奇和意外的东西。然而,在2010年代却出现了很多新鲜事物。当然,我们并不是说有多么不可思议的转变,但仍然有足够多的小变化,而这些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本身。幻想小说只是对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响。
图书出版的数字革命
古腾堡时代的结束?
与电子墨水(e-ink)技术传播有关的自动阅读设备的全球热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。但正是在2010年代,电子阅读器的大规模扩散变成了对“纸”的真正威胁。仅仅在头五年里,数字媒体上的书籍不仅成为传统印刷出版物的补充,而且在发行量上超过了它们。此外,一些书籍开始只以电子形式出版。
新的发行方式
阅读器的大规模普及导致了出版业的变革。西方出版商广泛采用按需印刷(POD)技术,即只有在收到客户的要求时才印刷新书。许多首次出版的作者的新书先以电子形式(通常是亚马逊的Kindle版)发行,几个月后才“以纸质形式”发行——出版商通过这种方式计算潜在需求并确定印刷量。接下来,安迪·威尔(Andy Weir)自行出版了他的处女作《火星救援》(The Martian)的电子版,这部书最终成为国际畅销书。电子图书形式的图书发行模式非常受欢迎。世界各地涌现出许多服务机构,利用这种形式新作者们能够自己发行图书,而不需要经纪人或出版商这样的中间人。因此,现在几乎一半的电子书销售来自于电子书出版公司。
幻想类期刊正在网络化
2010年代,全球幻想杂志的发行量稳步下降。期刊正逐渐全部或部分数字化。有时,它们与常规的印刷版本一起,以PDF或其他电子格式发行;但更多的杂志全面网络化。而且,这不仅仅是网站复制纸质杂志的内容——许多受欢迎的媒体,如美国著名杂志《轨迹》(Locus)和我们的《幻想世界》(Миру фантастики),都创建了自己的门户网站,在那里发布许多独家资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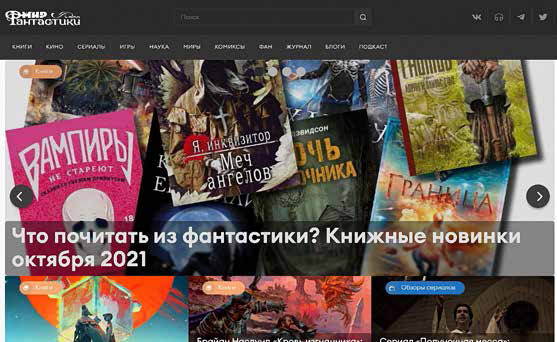 《幻想世界》官方网站截图
《幻想世界》官方网站截图
印刷书的死亡被推迟了吗?
全球市场对电子书和有声书的需求在2016年达到顶峰,当时它们几乎占了图书市场的70%份额。但到了2010年代末,以数字方式阅读的人数略有下降。在过去的三年里,它几乎没有变化,保持60%市场份额。倒退主要出现在文艺作品中,包括科幻小说。同时,数字领域内部也出现了重新分配——有声书的用户几乎是原来的两倍。
科幻小说:复兴
逃避主义不再流行了吗?
1990年代和2000年代属于长篇奇幻史诗,但在2010年代,科幻又回到了幻想文类的前列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奇幻小说在陈词滥调的重压下摇摇欲坠,只有暗黑奇幻(Grimdark)带来一丝新鲜感。也许科幻小说越来越受欢迎的主要原因,在于它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,并回应了我们此时此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。逃避主义已经不再流行——这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不同。已经成为主流的极客运动也发挥了作用:“科幻小说是为极客而设”的刻板印象已经成为过去。当代科幻是为每一个关心人类未来的人所准备的精神食粮。
太空之梦
过去的十年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太空的梦想。征服火星正变得越来越现实,开发小行星的计划正在进行中,空间探测器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木星和土星的卫星……现代太空小说从遥远的星系返回到太阳系,揭示出大众的好奇心——以及最重要的——希望。安迪·威尔(Andy Weir)的太空罗宾逊式的《火星救援》(The Martian)和尼尔·斯蒂芬森(Neal Stephenson)的大规模灾难小说《七夏娃》(Seveneves)有什么共通之处?这两本书的背景都是“近太空”,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“生存指南”(针对一个人或全人类),而且都在提醒我们:太空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有趣但极其危险的环境,与生命并不相容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早期太空小说的理想化幻想,而是具有强大防辐射功能的厚重宇航服。同样的(充满希望的,但非常危险的)太空在这十年中最著名的太空歌剧作品中得以展现,即詹姆斯·科里(James S. A.Corey)的《太空无垠》(The Expanse)。
另一方面,在新的太空歌剧中,太空只是事件的背景,其主要内容是人们将尖锐的社会问题带到宇宙最遥远的边缘。《太空无垠》(The Expanse)中的政治斗争,安·莱基(Ann Leckie)的《正义号的觉醒》(Ancillary Justice)中的“异类”宇宙模式,伊恩·麦克唐纳(Ian McDonald)的《月球家族》(Luna)中的黑手党部族的阴谋——所有这些对作者来说,都比火星上的苹果树和小行星带的矿场更为重要。
对生态的热情
全球变暖的话题已经成为主流议程的一部分,作者们以“气候小说”(Cli-Fi)的形式作出回应,描绘了生态灾难的前景。其中一个独立的子类型是“关于水资源之战的小说”——在未来的末世世界,饮用水已经成为比石油更有价值的资源,比如保罗·巴奇加卢皮(Paolo Bacigalupi)的《水刀子》(The Water Knife)。但生态活动家们正试图找到一条走出“气候僵局”的道路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称为“太阳朋克”(Solarpunk)的运动,与暗淡的赛博朋克相对应。太阳朋克文本喜欢为人类描绘一个新的家园,在那里行星被改造,地球被从人类活动的后果中拯救出来。比如,金·斯坦利·罗宾逊(Kim Stanley Robinson)的“现代乌托邦”《2312》描绘了一个几乎被生态破坏的地球的“逆向改造”。
民族幻想作品:一个多极世界
亚洲人的涌入
英语仍然是科幻的主要语言。幻想文学的“民族征服”始于华裔美国作家刘宇昆的英文翻译,他是被称为“中国版‘权力的游戏’”的奇幻系列《国王的恩典》(The Grace of Kings)的作者。正是刘宇昆向英语读者介绍了刘慈欣及其作品的中国现象。读者们继而对中国特有的“潮幻”(чаохуань)产生了兴趣,作者将其描述为试图表达现代中国的驳杂身份,这些对西方读者来说太奇特了。
由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作家的努力,亚洲也正在从内部征服英语文学。许多备受瞩目的处女作都是由亚裔作家创作的:李芳达(Fonda Lee)的《翡翠城》(Jade City)、匡灵秀(Rebecca F.Kuang)的《罂粟战争》(The Poppy War)和香农·查克拉博蒂(Shannon Chakraborty)的《铜城》(The City of Brass)。在过去的一年里,我们将第一本、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本东方小说选集——《一千个开始和结束》(A Thousand Beginnings and Endings)翻译成了俄语,编辑是“我们需要多元化书籍”运动的积极分子埃尔西·查普曼(Elsie Chapman)和艾伦·吴(Ellen Oh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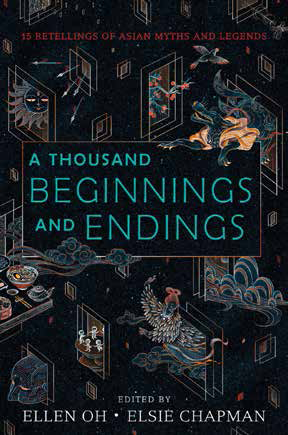 《一千个开始和结束》封面
《一千个开始和结束》封面
不仅仅是亚洲
中东与远东相距不远。很遗憾,在俄罗斯,阿拉伯语作者的书还没有被翻译引进。然而,在西方,海湾未来主义(Gulf Futurism)已经成为这十年的发现之一。在超级富裕的石油国家,几乎所有关于“近未来”的虚构和所有紧迫的问题都已经成为现实:从高科技世界中人的孤独,到“过度消费的危机”。以色列的小说与阿拉伯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呼应。我们知道的拉维·提达哈尔(Lavie Tidhar),他为人类的多民族未来描绘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——对以色列来说,这实际上已经是现实。
在过去十年中,另一个新的极点是非洲,这要归功于非裔美国人和黑色大陆的本地人的努力。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“黑命关天”(Black Lives Matter)运动表明,黑人不再等待“白人救世主”,而是准备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——而这种准备是由非洲未来主义(Afrofuturism)所表达的。非洲大陆在人类未来的地位、它的文化和神话都被非洲本地作家和移民所理解(后者数量更多、也更有名:泰德·汤普森(Tade Thompson)、恩内迪·奥科拉弗(Nnedi Okorafor)、马龙·詹姆斯(Marlon James)、N.K. 杰米辛(N. K. Jemisin),他们都在向黑人先锋小说家塞缪尔·德莱尼(SamuelDelaney)和奥克塔维亚· 巴特勒(OctaviaButler)致敬。
波兰极地
网飞(Netflix)的《猎魔人》(The Witcher)一定会刺激人们对波兰幻想小说的兴趣,这是当之无愧的:在过去的十年里,它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。亚切克·杜卡伊(Jacek Dukaj)和塞萨尔·兹贝肖夫斯基(Cezary Żechowski)探索地球和太空的后人类未来,罗伯特·M·韦格纳(Robert M. Wegner)和雅罗斯瓦夫·格热多维奇(Jarosław Gžendowicz)构建了宏大规模的幻想世界,克日什托夫·皮斯科尔斯基(KrzysztofPiskorski)和帕维尔·马伊卡(Paweł Maika)进行跨类型创作……一些有趣的波兰作者已经被翻译成英语,不少也被翻译成俄语,但似乎波兰小说的真正繁荣仍在前方。
性别:女性的时代
一场性别革命
在2017年的星云奖上,四个主要类别——长篇小说、长中篇小说、短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——均由女性获得:N.K. 杰米辛(N. K. Jemisin)、玛莎·威尔斯(Martha Wells)、凯莉·罗布森(Kelly Robson)和丽贝卡·花马(Rebecca Roanhorse)。该奖项的竞争者中也有许多女性。星云奖评委会被指责有政治偏见和“超政治正确性”:不仅有女性作者获奖,而且一些获奖者是少数族裔(杰米辛是非洲裔美国人,花马是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后裔)。在2018年,威尔斯和法裔越南人阿丽耶特· 德·波达尔(Aliette de Bodard)再次成为凯旋者。而看看近几年的雨果奖获奖名单就会发现,小说中的性别革命已经发生了,杰米辛、奥科拉弗、肖恩宁·麦奎尔(Seanan McGuire)、玛丽·罗比内特·科瓦尔(Mary Robinette Kowal)、阿利克斯·哈罗(Alix E. Harrow)、苏珊娜·帕尔默(Suzanne Palmer)、厄休拉· 弗农(Ursula Vernon)和其他女性都得了奖,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读者不熟悉的名字。
女性在文学中的胜利并不是对政治正确的赞美,而是相当自然的现象。现在,在各国的图书读者中,女性都占大多数——平均为60%。从逻辑的角度讲,她们一定有兴趣阅读那些理解她们的问题、并能够成为创造出令人信服的女性角色的作者。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由男性统治的“最后堡垒”——但它也终于沦陷了。科学和太空都不再被认为是“纯男性的追求”,粉丝中的女性也不再扮演成功作者的“美丽伴侣”(即可爱的配件)的角色,她们自己也成为成功的作者、编辑和评论家。也许在一段时间内,幻想小说中的女性看起来是“太多了”——但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根本不会觉得这是问题。
正是女性作家一度将性别作为社会建构的主题引入小说——想想厄休拉·勒奎恩(UrsulaK.Le Guin)的《黑暗的左手》(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)。当代女作家也渴望触及这个主题。例如,安·莱基(Ann Leckie) 在十年中最耀眼的太空歌剧之一《正义号的觉醒》(Ancillary Justice)中描绘了一个全新的社会,在这个社会中,性别原则上不是重要的和决定性格的要素。但强大而生动的女性角色在当代小说中数不胜数,从李允夏(Yoon Ha Lee)的《九尾狐赌局》(Ninefox Gambit)中的人物凯尔·查里斯船长(Kel Cheris),到罗柏·杰克森·班奈特(RobertJackson Bennett) 的《神圣之城》(Divine Cities)中的人物沙拉·科迈德(Shara Comide)和图林·穆拉赫什(Turin Mulagesh)。
被边缘化的人已走出了阴影
继女性之后,LGBT群体的成员在科幻和幻想作品中的角色占据了越来越自信的地位。这样的人物以前偶尔也会遇到——例如,在林恩·弗莱韦林(Lynn Flewelling)和理查德·摩根(Richard Morgan)的小说中,但我们越往前走,作家们就越大胆。因此,马龙·詹姆斯(Marlon James)轰动一时的“ 非洲幻想”《黑豹红狼》(Black Leopard, Red Wolf)也涉及同性恋关系,亚历克斯·马歇尔(Alex Marshall)的史诗《深红帝国》(Crimson Empire)描述了一个所有男人都是双性恋的世界,前面提到的作者李允夏是一名跨性别男酷儿,贝基·钱伯斯(Becky Chambers)的乐观太空歌剧《长途跋涉到愤怒小行星》(The Long Way to a Small, Angry Planet)中主人公爱上了一名外星女性。顺便说一句,詹姆斯是男同性恋,钱伯斯是女同性恋,所以他们只是在写身边之事。而肖恩宁·麦奎尔(Seanan McGuire)的获奖小说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门》(Every Heart a Doorway)的主人公甚至称自己为无性恋。这仅仅是个开始:以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正在慢慢变得显眼,这意味着幻想作品中这样的代表人物会越来越多。

《黑豹红狼》中文版封面
注释:
1 原文出自俄罗斯幻想媒体网站:http://nerohelp.info/19497-ftsr-brnds.html。
译者:三丰,南方科技大学访问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科幻产业、科幻与科技创新、科幻与城市发展、科幻史。(本文得到阎美萍的修订,特此致谢)
本文选自《世界科幻动态》2021年第3期
